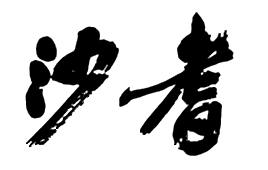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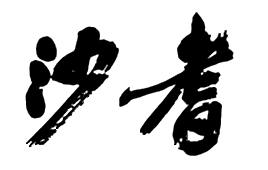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郭凤西
1)画坛内外
初到比国的时候,沙耆还偶尔参加一些留学生的活动,看望一下接待过他的王振纲先生。王先生是最早期的留学生,原来是学纺织的。三十年代初他开一家中国古玩礼品店,生意非常兴隆,对留学生特别热情照顾。
蒋仁搬到刘家,省了房租。他在皇家艺院表现非常优秀,和沙耆两人常常走在一起;但不久他转到巴黎去。此后沙耆埋头苦学、专心绘事,很少和中国同胞往来。
欧战爆发,1940年五月德军占领比利时。中国留学生大都回国,这时留在比利时的中国人很少。留学出身的还有钱秀玲化学博士、詹纯冰学农业的、华贻干从法国转来的工程师等人,他们都已成家,和沙耆也无往来。
有一位广东台山来的化学工程师黄瑞章先生,夫人是比利时人,黄先生是日本留学的,曾在此地糖厂、啤酒厂实习,以后自己开了个刺绣工厂,战前生意好时,雇佣四十多员工;德军来了,工厂停顿;黄先生平时也喜欢画画;又和巴斯俭常相往来;战时无事可做,就做了艺术学院的自由生,经常在校中临摹。这时沙耆已渐入佳境;仍常在校中走动,黄先生为人随和坦诚、渐渐熟识⑩。
总的来说,沙耆的社交生活是毕业以后开始,而交往的也都是艺术圈内的人士。以下逐一介绍。
史蒂凡(Stephane Rey 1910- )
在许多画展中为沙耆写画评的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而他和沙耆的交往就更加传奇。这位先生原是学法律、专攻犯罪学的,却以写恐怖小说而名噪一时。他又是商业家,开过工厂,主导过大企业;又始终醉心艺术,艺术评语的文章从未停笔。于是他集名律师、名小说家、大企业家、名艺评家于一身,而终身享有皇家学术院院士的荣誉。今年已九十出头,身心健康,看起来不过八十来岁。史蒂凡(Stephane Rey)是他写艺术文章的笔名;写小说的笔名叫"汤姆士、欧文 Thomas Owen " ,本名则是"Gerald BERTOT"
从他的画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沙耆的赏识。当年沙耆是他们家中的常客,给他夫人和儿子都画过像的。可是这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久事,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这时期和沙耆甚至和中国并没有来往。想不到当他谈起沙耆的事却犹如昨
夕。他们秘书说许多年来我们都熟悉了这个名字。史蒂凡仔细地翻开了1999年卡门艺术中心出版的"沙耆画集",非常专注。闭目沉思良久。交代秘书要查询的人物和资料,列出一个清单,就打电话给他的儿子:
[约翰,你把沙耆的两幅画像拍照送来]。
他的夫人早已过世,儿子住在乡下的别墅,两幅画像都挂在那里。他指着旁边的一张方桌说:
[当年沙耆来了就坐在那里,我太太弄个三明治给他,他吃得津津有味。
[唉!沙耆呀,光干活,不吃不喝;他法文说得很通畅]。
史蒂凡的住宅是祖传的老房子,一直住在这里。宽敞讲究,古董家具,大概几十年连室内的布置都没改动。
秘书另写一张单子给我,详列找寻的线索,约好下次来访的时间,参观了他的工作室,送我一本他的小说,"带入恐怖"(Thomas Owen,L'initiation a la peur,1942);并在门前合影,就再见了。
这天是九月二十,上午十点的约会,我先生陪我去的。他那天下午飞北京转赴山东老家探亲。晚上我一个人在家读史蒂凡送我的小说,真把我"带入恐怖",害得我心惊胆战,一夜未能安睡。
几天以后,他打电话来说,儿子约翰已把两幅画的照片送来,约我提前去看他,正好卡门艺术中心国际快递寄来的"沙耆画集"刚才收到。就带上一册再去看他。首先他重新专注地看画集,从头看起;然后,交给我两张照片:一张是他的夫人朱丽雅德(Juliette)的大半身坐像,中文落款"沙耆氏之作"另一张是两三岁的小约翰(Jean Gerald BERTOT),也是大半身坐像,题的是"天真烂漫",落款"沙耆作"。都是沙耆1942的油画作品。史蒂凡在相片的背面亲笔加上注释。
他看了我查证的资料,提出一些意见,指点进一步追究线索。又谈了一些当时画坛的情况,沙耆的作品、工作和生活景况。他表示要再写一篇有关沙耆的文章。就结束了第二次访谈。这一回他送我一本新出笼的小说选集"Thomas Owen,Oeuvres choisies I, 2000,La Renaissance du Livres" 。
人生是缘分,沙耆和他论交应在1940年前后。当时沙耆还是刚从艺术院毕业的学生,而他三十来岁、已经是人生事业的高峰。他用了大量的笔墨、极其深刻动人的词藻推荐沙耆,从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对他的真心欣赏,又介绍他认识许多艺术界的名人。世有伯乐而后有良马,沙耆在欧洲画坛的崛起,史蒂凡功不可没。而后者对前者的全力吹捧与提拔,出自于真诚的欣赏和爱才,看不出有其它目的。
巴尔杜诗(Georges BALTUS ,1874-1967)
不同于史蒂凡的、巴尔杜诗是专业画家、雕塑家、艺术理论家,学养深厚⑾,文笔也一样流畅典雅。当时他大约六十六岁,身体孱弱多病。沙耆和他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
有一回老人卧病在床,沙耆送一本英译的红楼梦给他病中消遣。他非常欣赏,以为这样的好书应该有法文译本,一定能打入欧洲人的心底。他说在这部巨著中,有那么多的人物,刻画精微;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动人的情节,安排巧妙;那么多的场景:楼台殿阁、树木花草…,都是绘画的题材,他建议沙耆为将来的译本画一些插图。
从书信中可以看出二人的交情。
1942年7月29日;沙耆因精神错乱送医院治疗,不巧老人也生病,他很着急,特别派人送些吃食。战时的食品是很贵重的。并且在信上告诉他:"我去过你家,看你那些作品是否安全,这方面你可以安心。你的门户是警察锁上的,将来回家的时候一切如旧。要听医生的话,才能尽快复原,重新工作"。
到8月30日,老人病好了,再去沙耆住处,知道他已回来过,并且不久就会出院回来。信上交代他很多细节,希望看见他的时候,已完全康复。像一个老父亲对儿子的关怀。
古德丝妲夫人(Madame GOLDSTEIN 1913-)
沙耆在史蒂凡家里结识了这位太太,也是学画的,今年八十七岁健在,对沙耆印象深刻。她说:有一天沙耆在她家做客,要吃她自己做的草莓果酱,她去厨房准备,就这么一会儿,沙耆用两滴水,给她画了一张水墨画像,非常生动。她一再形容"真的是只用了两滴水画的"。这幅画一直挂在他们的客厅里,后来几次搬家不知去了哪里?
柯兹(Serge CREUZ)
是艺术界的名人。比京自由大学(ULB)法律系毕业的,也走到艺术的路上,他做皇家艺术博物馆馆长,也评论过沙耆。他发起组织"拜高纳艺人之家"(Maison de la Belcone)。小画廊(La Petite Galerie)的老板王楼(Van LOO)常去;沙耆在那里结识一些艺术界的名人;王楼的女儿是比国之声(ECHOC)专门报道艺术活动的记者,所以他们的"小画廊"当时是声望很高,在那里开画展,一定要有相当的水平;沙耆在那里的展品大概都能卖掉。
迪瑞亚(JeanTHIRIART)
这个年轻人有一班爱好东方文化的青年朋友:王德诗(Van der Hscht)是教中文的,彭法迪夫妇(Bonfanti)法律系毕业的,米娃儿(Jose Mirval)学文学的;李朋(Jean le Bon)对佛学有兴趣的,奥恺特(Requette)小姐、乔治雅德(Georgette STUX)小姐等人,都不过二十来岁。他们很诚意的与沙耆交往。
沙耆和他们来往,参加他们组织的文艺活动,每星期下午,在黄金方场九号(Grand Place 9),举行有关中国文化的节目。内容包括:艺术、文学、音乐、科学等。
1941年10月11日星期六这一天的节目如下:
迪瑞亚本人讲:"中国文字的像形意义"。
沙耆讲:"中国各民族的景观,介绍山区的旅行的经验。
乔治雅德介绍中国诗词。
王德艾特VANDERHECHT是语言和文学教授,讲"孔子的德道学说"
米娃儿(Jose Mirval)做接待。
这一群青年人,今天还有些健在。迪瑞亚后来做了光学家,在布鲁赛尔开设光学器材公司,一年前过世;米娃儿退休后住在法国海边的养老公寓;乔治雅德可能还活在世上。
2)红颜知己
那个时代的欧洲少女,钟情于外国学生的例子很多,而且大都是温柔贤淑型的。吴作人和李纳的爱情可说是轰轰烈烈;李纳温文典雅、而又明媚坚毅,以至把生命也交给爱情和家庭。同时代的留学生娶到这种典雅的比国小姐,或者嫁给比国男士的例子太多了,像上面提到的黄瑞章先生、华贻干工程师、钱秀玲、詹纯冰女士都是夫唱妇随、白首偕老的。
沙耆在学生时代,没有风流韵事,他一心向学,麻烦事避之惟恐不及,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
一出校门就挤身于艺术家之林。正是人生的黄金年代,有些漂亮的比国女孩欣赏他的艺术和风采,对他表达了非常细腻的感情。
上面提到的乔治雅德在1941年10月27日写给沙耆的信上说:
昨晚我和妈妈发生口角,因为她坚决反对在暖气弄好前继续跟你上课。一旦可以重新开始,我会立刻通知你…
星期天我会去听音乐会也许我们可以在散场的出口见面…
不久以后的另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今天下午我对你不够体贴,衷心懊悔;都是因为这段日子我是太紧张了。希望你不要难过,我一点也没有怪你的意思。
不管我遭遇到什么,请你永远不要内疚,因为环境是这样的,谁也无法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再改变。
不要为我担心,目前最重要的事是继续准备你的画展。继续画出那些我崇爱的奇妙事物,那将会使你成为我钟爱的伟大画家。
乔治雅德
此姝秀外慧中、感情细腻,她鼓动沙耆放开一切专心绘事,将来必成大器。沙耆经常在身边的一张少女侧面像片应该是她;从信上看出她母亲是反对和沙耆交往的。
这一年开始他的画受到比国人的赏识,声名雀起;各地画廊纷纷来接洽展览。虽然一度病发住院治疗,加紧工作,连年到处参观或举办个展。
和乔治雅德的母亲不同的,也有父母鼓动女儿和沙耆交往的。
1942年5月,沙耆因故未能参加一个朋友的晚会,他叫花店送一束花去表示歉意。一个名叫玛丽露意丝(Marie-Louise)的女孩给他的信上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沙耆先生,
你送我的鲜花是多么美丽啊!既鲜艳又亮丽,我可以从中看见画家的慧眼。你这份亲切礼物使我感动。
你有没有收到妈妈的信,她问你为什么五月十二日的晚会你没来?我们十分惊异在你的朋友中未能看见你。我们还请了巴尔杜诗(BALTUS)先生,以为那样在介绍生客时你可以更自如…
我最担心的是你可能误会我们不是你真诚的朋友。爸爸和妈妈都欣赏你的作品,常常谈到你,如果他们能为你做点什么,他们将十分乐意。请相信你永远是我们家中极受欢迎的客人,请接纳我的好意
玛丽露意丝
沙耆这时可算得青年英俊,风度翩翩;自己又颇注意外表和体貌;常想着带一束花、一盒糖。他这种心性和习惯,其来有自,大概是血液中带来的吧:心思细密、常常想到别人、想到别人的好处;出国前、出国后、对家人、对外人,出自本性的自然反映;并不是由于这个人今天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他给人的印象是温文有礼。史蒂凡(Stephane REY)回忆说:"沙耆穿着十分得体,常带着纯真的笑容,讨人喜欢";古德丝妲夫人(Madame GOLDSTEIN)也有同样的记忆,他说:"沙耆,真诚、爽快、明快,我们一家人都喜欢他"。中国人与外国人交谊常常面带笑容;但笑要发自内心,给人有以上的感受才算恰倒好处;但这又不是装作得来的。
沙耆当时的条件是优越的;时势环境是混乱的,全世界都在打仗,遥远的祖国已经血战了许多年,父母妻子如此遥远。处身在这样的境地,人很容易卷入感情的纠纷。要能洁身自好、洒脱自如,需要非常的节制;在我们掌握的资料中,并未发现他陷入情网,不能自拔。沙耆回国后把乔治雅德的相片随身携带,可见他是十分珍视这份感情;可是他们之间除了这两封还不够称为"情书"的信件外,我们无法证明他们的交往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也没有发现沙耆在如此风光的时代有过其它特别关系的女人;也许还未发现,但我们也不愿再去追寻。
是什么力量能使他如此坚定呢?是传统的礼教观念?是对于画的执着?不错他天生是画画的,他的爱情是画画,无可取代!可是天生的画家也是最激情、最浪漫的;所有这些潜在的意识、不同属性的内涵,互相排斥;在他心灵的深处,不停地激荡倾轧;外表上愈克制,心灵中越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