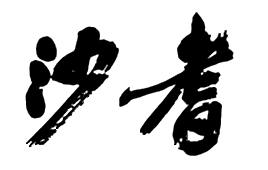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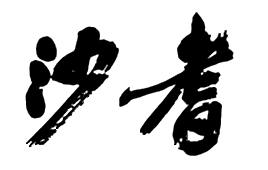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徐水平/录音整理

沙耆(1914-2005) 生于浙江鄞县沙村,名引年,字吉留。1929年入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1932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3年因政治原因被捕入狱一年;出狱后赴杭州西湖艺专求学,即由沙孟海取名耆,并推荐至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师从徐悲鸿;1937年初经徐悲鸿介绍,自费留学比利时国立皇家美术学院,入巴斯天教授(Prof. A. Bastien)工作室,1939年毕业并获"优秀美术金质奖章";此后曾与毕加索、德立克(Trink)等同场展出作品,也曾在比国举办个展,《吹笛女》一画为比国皇后购藏;1945年底赴英国、荷兰等地旅行写生;转年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旋即回国养病。徐悲鸿欲聘其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而未果;1947年回归故里,由母亲照料;其母去世(1964年)前将其携归作品百余幅赠与浙江省博物馆;1981年移居鄞县韩岭镇,休养于学生余毅家;1983年5、6、9月,浙江省博物馆、上海油画雕塑创作院和首都博物馆先后举办"沙耆画展",《自画像》等作品由中国美术馆收藏。是年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明年再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85至1996年间,画作颇丰,这期间曾由余毅陪同游览浙江、吉林诸名胜;2001年3月,中国美术馆为其举办"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2005年春病逝于上海,享年91岁。
徐翎(以下简称徐):水先生,沙耆早年在欧洲挺活跃。他是不是中国惟一一个和毕加索这样的著名人物同场展出作品的人?
水天中(以下简称水):不止他一个,还有常玉、朱沅芷等人。常玉他们一直留在法国,沙耆回来了。他回国后完全脱离了主流艺术圈,处境跟当时国内所有的画家都不一样。经过上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性整合以后,几乎没有一个画家能够置身于当时的体制之外,特别是油画家。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沙耆不是精神错乱的病人,他自己在那里一会画人体,一会画花草风景,肯定会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抓起来。处于这样一种体制外的状态,他反而很"自由",在50 - 70年代这30年里,他完全是以无所顾忌的心态画他想画的画。
徐:他一直是这样持续下来的吗?
水:就是这样。熟悉他的人,包括照顾他的人说,沙耆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犯病时说话办事就有点神神叨叨,甚至更严重。他把自己住房的墙皮、门板上都画满了画、涂满了字。台湾的历史博物馆办的展览我去看了,其中就有很多他画在门板和墙壁上的作品。那时候,他随便抓着什么都在上面画,还包括书本、报纸,他全画满了。作为一个画家,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也是他生活的需要。他也只能通过绘画来宣泄和抒发自己一生的想法或情绪。
徐:他的病是在国外引发的吗?原因是什么?
水:早先我听别人谈起过,那时我自己估计可能与他的婚姻有关。后来知道他在国外已经出现症状,但很难说原因是什么。有人在比利时查过他的档案,据说是这样的,沙耆在比利时的时候,有一次他跑到一所教堂里,正好教堂里没人,他跑到了教堂的祭坛上,四处看,到处找。神父觉得很奇怪,问他在找什么?沙耆两眼发直地说:"我找我的上帝。"神父就找来当地警察把他送到了医院。这是他第一次发病,也是现在所知的最早记录。
徐:是这样。沙者在国外的作品都带回来了吗?
水:就我所见他的早期作品主要有30年代他在比利时留学时的自画像,还有一些风景和静物。保存沙耆作品的地点主要有:浙江省博物馆,那里保存最多,是他的家人捐献的;还有中国美术馆,在北京办完展览以后,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几幅他的写实作品;沙耆的后期作品绝大部分在台湾的画廊。
徐:他最初的作品好像写实成份多一些。
水:的确如此,那些作品显示了他的技法功底。沙耆的老师巴斯天的作品曾到中国展览过。那是30年代抗战以前在中国举办的比利时画家作品展,规模很大,而且很正规,是由比利时政府出面举办的一个展览,当时在上海和南京都引起了很大轰动。巴斯天是参展画家当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美研所旧藏的老杂志上还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而且刊载有巴斯天的作品。现在看起来,沙耆早期画的静物跟他老师的作品还是很像的。吴作人早期的静物也能看出那个味道。但是和吴作人比起来,沙耆显得更自由些,吴作人更严谨些,其中也有年代不同的因素。
徐:很多在国外学油画的画家,回国以后画的画和在国外期间的作品相比较,往往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色彩感觉完全不一样,甚至造型能力都可能有很大的落差。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个别现象,好像一批人都是如此。这一直是一个让我疑惑的问题。
沙耆江上的帆影油画1994(图)
水:那时留学回来的人,如果能够保持留学期间的水平就很不错,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能有所发展就很不简单了。例如吴冠中,现在有些人对他颇有微词,但是我觉得他是那些留学生里面仅有的那么几个保持绘画水平的画家之一。
徐:李铁夫就有那种倾向。他回国后给人画的肖像,艺术水平跟他从国外带回来的作品真的不一样,所以有人怀疑那是不是他自己的作品。
水:最明显的例子还是一代宗师徐悲鸿。他在国外画的人像多好,特别是人体;再看他在国内画的、最近市场上拍卖的几张女人肖像,还有他给广西白崇禧、李宗仁等人画的二个人的骑马像,现在来看就是业余水平,美院附中的学生也不会画成那个样子。
徐:这能否说明油画的要求跟我们的本土艺术在感觉上还是有某种隔膜?
水:我最近连着去了两次法国,看了法国的奥赛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跟前几年有所不同,现在他们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许多写实派画家的作品也挂出来了,包括所谓的折衷派、学院派,当时是受到排挤的。在印象派出来以后,竟然还有人搞那些东西,似乎很不自量力。也许法国人现在发现那些人画得不错,就把他们的作品又拿了出来。我看了那些画以后,说老实话,我发觉那一代的中国画家,像徐悲鸿、吴作人,还有吕斯百,他们并没有把洋师傅的东西学到手。在学习的意义上来比较上世纪50年代留苏的学生,后者倒是把老师的东西学到手了。其实苏联老师的水平不是很高,然而当年留苏生回国以后,在造型能力、色彩感觉等方面,现在都还保持着。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个是因为早期那些留欧学油画的人在出去之前的起点比较低,有的根本就没学过画,像徐悲鸿虽然多少受他父亲及乡下一些画师的影响,但毕竟很有限。所不同的是那些人的文化素养比现在的人要高,可在艺术技巧方面比较差。
徐:也就是说,那一代人对油画技巧的理解以及对油画绘画性的体会是比较弱的。
水:还有一种情况。中国学生都很聪明,许多人学了一年多就画得很好了,可以通过考试,有的人还得过奖,那样很快就可以毕业。还有一些学生,因为画得好,直接就念三年级--现在还有这样的。而且,当年他们在国外的学校里一般只学三年,学校在夏天和冬天还要放假,这样他们学了三、四年左右就回国了,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也就很难谈得上深入和巩固。当时的留学生回国后往往又立刻成为教授,加上时运不佳,赶上连年战乱,特别是抗日战争,这样的社会环境没能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进一步推敲、完善他们曾经学到手的油画技巧,很快他们的学识和技艺出现一种"回生"状态。
徐:就像一个人学外语,要是不用,过两年也几乎就忘光了。
水:艺术创作需要一个文化环境。就像在课堂上画的习作,大家都是那样画,彼此间会互相影响。一个在国外留学、生活多年的人刚回来,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有点洋里洋气的,说话、抽烟、喝茶都那个味道,可是过一段时间那个人也就恢复原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这些画家在艺术上有一些希望,并不是说希望他完全保持留学时的习惯,而是希望他天性里面,或者在艺术气质里面的某一种因素能够发挥出来。
徐:这点沙耆可能保存得比较多一点,其他大多数的画家或多或少可能都受到外界的影响。
水: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吕斯百。他是农村出来的,人非常朴实,非常温和,在他的静物画和风景画里面都保持着这些天性,而且他在法国时也没有明显的追求,不像徐悲鸿,决心要搞古典主义的艺术,吕斯百他什么都要学一点,回来以后反而还能继续把他的本性保留住。从环境这方面来看,徐悲鸿的才华也被糟踏了。他本来的想法是要画出古典主义的重大历史题材巨作,在他现有的作品里面,《田横五百士》、《奚我后》、《愚公移山》这几幅画代表着他的奋斗目标,而其他画猫、画马等作品都是些应酬之作。可是现在大家一提徐悲鸿就说他是画马的。应该说他的马有几张好的,可是大部分不好。
徐:这样看来,对沙耆而言,当外界不能对他产生任何影响时,他反而能保持并发展他在油画上的绘画能力。但是他是不是也有以上那些变化呢?
水:有变化。包括造型能力、色彩的领悟能力,他后来并没有把他在留学时的状态完全保留下来。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刚好把自己感兴趣的那一部分推向极致。这正是现代艺术的特点。现代绘画不就是这样吗?把绘画的某些因素推向极致,比如把色彩推向极致,把结构推向极致,就形成了所谓的野兽主义、立体主义等等。就沙耆来说,他并没有一种理论指导着自己,他是一种完全自发的和随心所欲地发展,是天性使然。艺术如果脱离了个人的天性,也就不成为艺术了。由此看来,沙耆保持了这些,他始终把他的绘画和他最隐秘的天性、情感融合为一体,因而他的欲望,失望和悲哀都能够通过作品看出来
徐:沙耆后半生是在偶尔癫狂、偶尔清醒的状态下度过的。他对自己的命运,或对自己的创作有过什么总结性的或评价性的认识吗? 水:我没看到,别人也没提到过这样的材料。但是从他的画和他写的一些东西看来,他一直对自己在婚姻、爱情中遭到的挫折耿耿于怀。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情况,冯法祀和沙耆是同学,他曾参加沙耆的婚礼,他说:"沙耆的新媳妇太漂亮了!"他认为沙耆的精神错乱和沙耆离妻别子出国求学并最终失去妻子有关系。
徐:关于他对自己的认识,就没有留下他自己的什么说法吗?
水:早期有一点零星材料,晚期没有写过完整的东西,包括他的经历、艺术,他都没有写过。他有时信手乱写,什么"省主席总司令沙耆……建都杭州,迁往居住"之类的话;他也题诗,比如把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写成"沙耆画虎画风景,一张一笔思华年……"。他没有被绑赴刑场枪决,确实得感激当地农民的宽厚。关于他的艺术思想,只能根据他的图作大体归纳。
徐:为什么大家都会对他产生兴趣?是因为他的画,还是因为他传奇的一生? 水:主要是因为他的画。比如美术界里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原先多少都听说过沙耆,但许多人以为他早死了。
徐:您最早听说他是在什么时候?
水: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次展览,以后就再没任何消息了,像杂志、报纸,都没有再提到过"沙耆"这两个字。我就想他可能早就死了,后来听说他还活着。再一个就是从1995年开始,经过中国美术学院胡振宇、舒传熹教授的指引,台湾一家画廊(卡门艺术中心)收购沙耆的晚期作品。他们把沙耆的作品印成很漂亮的画片,在1998年组织座谈会作欣赏和述评。在此之前,组织和主持那次座谈的理论家如钟涵、范景中、曹意强等,也不了解中国还有这样的画家。大家总觉得中国的老画家都是那种老老实实作画的人。中国还有这样一种完全自由和狂放的画家,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看过他的画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个人曾经精神错乱,这给他本来与众不同的画增加了一点传奇色彩,人们的兴趣就更大了。现在看来那次座谈会确实是办得很成功的。
徐:这种被历史遗忘的人物不在少数。但很多人就是没有任何消息了。曾经有人想挖掘这些人,想好好介绍一下他们的经历以及艺术创作,但一直没做起来。您觉得重新挖掘历史有意义吗?
水:还是有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也曾经想为三四十年代那些老画家出书或者办个展览。当时好多人都还活着,包括林文铮、刘海粟、秦宣夫、倪贻德的夫人等,我们还去访问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沙耆在世,要是知道我们也会去看看他的。后来,因为没钱,也没人支持,我们的想法还是没能付诸实施。不像现在,可以和画廊联系,收购点作品,他们很愿意干。
徐:就像湖北的李青萍,全都是画廊给"做"的,最终他们把几乎湮没的中国早期油画史这块给"做"起来了。
水:80年代《美术思潮》杂志上曾报导过李青萍,她当年还是很活跃的艺术家,后来又忘了,一直到她死亡。
徐:是不是跟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状况有关系?
水:应该是有的。以往什么事情都要"组织"去操心,而"组织"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管到。你要说湖北有个捡垃圾的老太太会画画,要"组织"去关注一下,这对"组织"有点太苛求了。
徐:被遮蔽的画家,和他们的画风也有关系,对吗?
水:当然有关系。那时如果一个画家的写实功夫特别棒,他早就画革命历史画了,大家就不会淡忘他,他也不会被遮蔽。对沙耆作品的艺术价值,基本上大家都是承认的,之所以没有出现评论家完全否定他的这种情况,也在于还保留了他早期那些非常严谨、能够看出写实"功夫"的画。这就像罗素曾经说过的:写文章完全用不着写出那种很讨厌的、很刻板的学术论文,完全可以随心去写:但是他又劝告青年学者,开始时要写学术论文,罗素说由于他有关于数理逻辑的著作,别人才不敢否定他那些随性写作。
徐:对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之谈了。很多像沙耆这样的人都已经走了,对我们的油画史来说,活着的资料越来越少。有些人物用我们以前的观念去看,没办法把他们给归纳进去,因为他们的创作和人生经历都超出了主流的价值观念。关于沙耆的话题,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挖掘的吗?
水:对于沙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他的画放在近现代绘画史系列里面去,就是我们一开始谈的,他有别人所无法替代的位置。他的创作方式与同时代的主流创作方式对照,在他的创作里面我们刚好能找到主流创作里所缺少的、被限制的以及被扼杀的那些东西。当然主流的体制也为画家提供了很多方便,物质的、时间的条件。这些沙耆都没有,他没有享受任何这些优惠。如果当时的画院能有点先见之明,给他画布,画完了也不用给钱,国家收回来,沙耆也会很愿意。画家总是愿意在很好的画布上作画。
现在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发现他在比利时参加展览的那批作品,那些是他很重要的作品。他那时参加过很多次展览,而且据说当时他的画卖得不错。在欧洲某些地方说不定还能找到他的作品。台湾有画廊曾派人在那里呆了半年挖掘这些作品,可惜没有找到。沙耆这一阶段的作品如重新发现,能更完整地了解他的艺术历程。过去国外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美术不太关注,中国近现代美术成为一个学科,中外是同步的,这是最近十年的事。而沙耆显然是具有美术史意义的。口(徐水平/录音整理)
ART OBSERVATION
沙耆油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