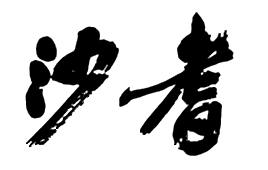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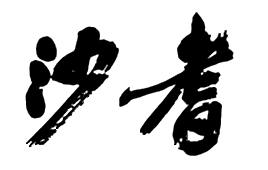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水天中
一、沙耆和他的时代 沙耆原名沙引年,1914年出生于浙江鄞县沙村,1930年入上海昌明艺专学画,1932年入上海美专,1933年6月,因参加反帝抗日宣传活动被捕,并以“危害民国”罪被控。经嫁人交保后出狱,入杭州艺专学习。为躲避上海法院追究,曾藏匿于浙江杭州郊区宁波四明会馆,并更名沙耆。1934年经其族兄沙孟海介绍,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拜见徐悲鸿,徐氏允其留校,以旁听生资格学习绘画。1939年以优秀成绩毕业,并两次获得“优秀美术金质奖”。沙耆毕业后继续在布鲁塞尔从事艺术创作,其作品曾与毕加索等著名画家一起参加“阿特里亚蒙展览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沙耆滞留比利时。曾在Petite Galerie等处举办个人画展。1942年,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购藏了他的作品《吹笛女》。 沙耆在比利时留学时的老师是巴斯蒂昂(Alfred Bastien),他也是吴作人的老师。吴作人和沙耆留学之前,巴斯蒂昂已经被认为是比利时印象派的代表画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按照由教授轮流出任院长的制度,巴斯蒂昂一度担任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据吴作人介绍,巴斯蒂昂是“比国现代大师中最崇拜中国过去优越文化,最爱与我国人士接近着”。在他执教的班上,曾经同时有过11个不同国籍的学生,吴作人就是其中之一。1913年巴斯蒂昂曾到中国浏览,并作写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年界41岁的画家坚请超龄服役,战斗间隙在战后作战场写生。战后,他在此经历基础上,创作了周长150余米的战场全景画。吴作人曾参加绘制乃师承担的壁画工程。1934、1935两年间,比利时驻华使馆先后在上海和南京举办比利时现代绘画展览,这一展览被国外艺术史家看作20世纪前期在华举行的欧洲画展中规模最大的展览。巴斯蒂昂为比利时国王亚尔佩一世所作骑马肖像和花篮果盘静物参加了展出,从图片上可以看出,沙耆早期间所作的静物,确实承接了他的老师的绘画风格。吴作人在为画展撰写的文章中介绍巴斯蒂昂的作品时,也指出简洁放纵的笔法、丰富奇幻的光色是其风格特点。沙耆的点画自在、不拘绳墨的笔触,的确院子乃师意趣。 沙耆在比利时学画的时候,现代主义艺术风潮已经席卷全欧,布鲁塞尔一度成为超现实主义艺术活动的中心,像巴斯蒂昂这样的学院派画家,已经不再对艺评家有吸引力。 沙耆在比利时的时候,哪里活跃着一些重要的画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以奇异的幻想使人刮目的恩索尔。恩索尔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在吴作人、沙耆去比利时的年代,他已经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他不断地挑衅世俗趣味,以种种出人意料的形式表现现实世界的“邪恶愚蠢和杂乱无章”。这种瑞的批判态度导致他与主流艺术界一次又一次的冲突矛盾。晚年,他终于被社会接受,比利时国王册封他为男爵。 另一位是被称为“神秘显示主义”着,并被视为20世纪比利时最重要画家的马格里特。马格里特也曾就学于布鲁塞尔美术学院,离开学院后与几位文学家、艺术家组成一个超现实主义小组。后来迁居巴黎,他参加当时的超现实主义活动,于30年代初回到布鲁塞尔。当我们的沙耆在布鲁塞尔美术学院跟随巴斯蒂昂学画时,马格里特正在布鲁塞尔探讨现实物象与绘画的关系,陆续画出那些亦真亦幻的奇特作品,例如餐桌上的盘子里有一片火腿,火腿中间有一个向观众凝视的眼睛,等等。马格里特从巴黎回到布鲁塞尔之后,也经历了一段寂寞的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的艺术才智才得到广泛承认。那是,沙耆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正在浙江乡村养病。 在马格里特的追随者中间,最著名的就是德尔沃。德尔沃原先在布鲁塞尔学习建筑,后来沉醉于印象主义绘画,开始了他的绘画创作生涯。1936年,也就是沙耆到比利时一年后,德尔沃“发现”了马格里特,在马格里特的神秘现实主义启示下改弦易辙,以自己的独特放歌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开拓出另一片空间。他所创造的那些梦游者似的女郎,成为20世纪人类最难忘却的形象之一。 沙耆在比利时居留时期,现代主义画家在布鲁塞尔十分活跃,他当然会接触并了解前述诸人的艺术观念与绘画作品。虽然他作为巴斯蒂昂的学生,没有离开写实主义,但从他40年代的几件作品中可以感觉到,沙耆比在他之前留欧的中国学生如吕斯百、吴作人、李瑞年等人,更加理解和靠近现代艺术。 虽然沙耆在艺术上学有所成,但由于大战期间来自各方面的精神压力骤增,不幸酿成精神疾病。1946年10月,沙耆带着他的大批作品回国。徐悲鸿没有忘记这位有才华的学生,聘任他为北平国立艺专的教授。但沙耆未能北上赴任,他滞留在他的故乡,他无法适应预料之外的家庭变故——老父病故,妻子带着儿子参加了革命。这给沙耆无法承受的打击,他本来就不健全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从此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周围的人称他“疯子”,没有人把他当艺术家对待,他与艺术界失去了一切联系。 沙耆之被遗忘,其直接原因当然是他的疾病。他回国后适逢中国社会的巨大动荡,先是三年解放战争,接着是接连不断的政治变动,人们无暇顾及这个病中的画家。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坠入遗忘之雾的知识分子远不止沙耆一人,但沙耆不是社会需要将他遗忘而被遗忘,既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被有意识地遗忘,他是由于疾病而被遗忘。按理说,他有一大批作品在,即使“现在的”沙耆与美术无缘,“过去的”沙耆也不会消失的。但50年代以后,在美术界担任领导职位的一批艺术家吧一切艺术问题都与政治问题挂起钩来,他们对美术家和美术作品的鉴定,都坚持毫不含糊有及其偏狭的政治标准,即高扬所谓“为政策服务”。以沙耆的艺术状态,他要突破被遗忘之雾,则不仅仅是健康问题,而必须等待意识形态局面的变化,等待一个较为宽容的文化环境的到来。 沙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83年5月,沙耆画展在杭州展览馆举行,展出的是他1946年以前的作品。画展在杭州举行之后,又在上海和北京举行,人们对他的这些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沙耆的亲友为展览的顺利举办和展览带来的结果深感欣慰——沙耆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员,每月的生活补助费(由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发给)由“文革”前的四十元增加到100元。 但展览之后的沙耆,除了按每月领取100元“工资”之外,并没有什么变化。他似乎又一次坠入遗忘之雾。浙江博物馆将他的作品存入库房,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他的三件作品,从此沙耆被归入三四十年代的画家行列,他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和那些早就离开的人世的画家并无二致。 其实沙耆的再次被遗忘并非意料之外的事。80年代初期中国美术界官员们的承受力还十分脆弱,首都机场壁画中的半裸妇女形象,曾经引发难以收场的巨大风波,美术界领导所能接受的,只限于沙耆早期的写实作品。据沙耆之子沙天行回忆,在“审查”展品时,浙江省委书记曾对几幅裸体画大为不满,说这种画“有伤西子湖的风化”,“怎么能拿到红太阳那里去展览”,结果展览改为“内部观摩”。可以想见,如果1983年把沙耆患病后的作品拿去让领导审查,其后果将不是把公开展览改为“内部观摩”就能了结的。了解沙耆的人适可而止,不了解沙耆的人也未作深究。这就是沙耆被发现和再次遗忘的背景。 两度被遗忘,竟然成全了沙耆的艺术。50年代,他没有像许多同行那样在艺术上改弦易辙,去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60年代,他既没有被打成“牛鬼蛇神”,更没有资格做“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去“敬绘”“宝像”。这使他保持着与艺术之间的纯真关系,使他得以继续用画笔宣泄心头波澜,而不必像其他画家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地附和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 于是,形成如此辛辣的历史讽刺:健康的人惋惜他们失去了精神病患者才能享有的宁静和自由。 现在,人们都感受到当时美术体制的弊端。这种弊端竟然以正常画家的不正常创作状态,与不正常画家的正常创作状态之间的对比呈现我们的艺术史上。
二、身边的现实和心中的现实 沙耆早年曾经参加革命活动,宣传抗日救亡。为此曾被当时的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判刑,经亲友相助,家人以蒙混方式敷衍当局追查,使他逃脱囹圄之灾。他告别新婚妻子孙佩君离家远行,在欧洲留学期间遭遇世界大战,日本侵略军占据江南,他成为帮过沦丧、无家可归的游子。战争结束后从欧洲归来,等待他的是妻离子散的场面。此后,一直在浙江乡村度过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的时日,亲身经历了大陆农村政治管束最严格,而经济状况最艰苦的日子。这些生活片段成为他刻骨铭心的伤痛。疾病可以扭曲、搅乱这些记忆,却不能消除或解开深藏于心的疑窦。当心智清醒时,他可以暂时淡忘这些伤痛,以现实的眼光看待时世;在犯病时,种种伤痛涌上心头,给他既强烈又纷乱的刺激,形诸文字图画,便有那些时而身沉瑰丽,时而扑朔迷离的作品。 40年代归国以后的作品题材,以风景、静物和女性形象为主,有许多事写生或依据对真实物象的印象所作,也有一些是在现成的图片以及他的记忆基础上的发挥,这些,大都属于后者(指犯病时所作)。 他所描写的也就是他不可能抛弃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感触与形象。他的绘画作品金额那些不堪卒读的断简残篇,就是这些心绪的双重解释。 无限熟悉又无限陌生的家乡故里,它既逼近又遥远。青年时代去国离乡之后,他实际上就已失去了家和国,他苦苦思索又找不到答案: 上海相送别,于今四十三年,沙耆归不归/沙耆岁(虽)在老家宇内无异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童村桥边野草花,沙村巷口夕阳斜,旧时沙家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他反复念叨“家”与“国”: 沙耆是有国有家的人不能保家救过是有罪/有国可归有家可归/门户不能无条件开放一日二十四小时让敌人外人无条件自由出入/门户在贼人手里是破家国界在敌人手里是亡国……我一定是门户和国界管制人…… 还有那些永远无法从心头抹去的女性,她们那种既诱惑人又带有警戒性的表情和颜色,牵扯着沙耆情感上的创痛。他一直不能接受妻子离他而去的事实,对1949年的“协议离婚”,在内心深处根本没有接受。对女性的渴望和对女性的反感,困扰着离群索居的艺术家。于是,青年女性形象总是附着于难解的爱恨情结: 夫妻不相见,嫣知四十载,昔别与君婚,子孙忽成行,耆非会面难,中欧两茫茫/上海相送别,于今四十三年,沙耆归不归/沙氏窥帘孙家少,阿衡留枕沙耆才/嫁得沙领业,朝朝误房事。……病没有女人罪没有爱人罪有一个女人无罪上海法庭委屈遗精病婚姻无病四十年四十七年…… 在他那些漫无涯际的荒唐言语中,除了个人家小之虑,也对历史进程的感叹和疑惑。他去国离乡之前还背负着“危害民国”的罪名,回国后,等待他的却是残酷的内战。转瞬之间,使他承担罪名的国体竟然烟消云散。而贫穷、压抑的生活境况和纷至沓来的政治运动,更使他如坠五里雾中:……因为上帝在中华所以三十五年前回国四十七年以前被告危害民国案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鱼是我每日三百零用熊掌是民国三百亿国民币作废人民共和国出版三百亿加八十五亿……。民国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花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民国亡/国共凭陵杂风雨,国共白刃血纷纷/国共弓箭各在腰/旧业已随民国去,更堪江上剿匪声/……商女不知民国亡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这一类狂想,只留在他信手写下的文字中。绘画对于他属于另一种思维方式,在哪里,他顺从绘画的运动规律,以他所习用的方式驰骋幻想。如果说那些文字是沙耆“不愉快的梦”,那么他的画可以说是“愉快的梦”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那些不愉快的梦“属于潜意识的某个愿望所提供”,而他的这种愿望,乃是一个“被禁忌的冲动”。 天才与精神病或者精神病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不会使人厌倦的问题,因为每一个时代都出现过精神不正常的天才。19世纪意大利的以为著名精神病专家C.隆布罗索曾就这一问题写过一系列论文,他从许许多多伟人的传记材料中找到他们存在精神病症状的证据,并由此得出天才飞入形成与癫痫有关的结论。但随着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进步,人们发现以C.隆布罗索为代表的观念,缺乏科学上的严密论证,而且常常把性格和脾气的乖僻解释为精神疾患。进入20世纪以后,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规模的统计,他们发现历史上的天才人物,是在完成了他们的创造事业之后才得病的。一方面,神经病理学的调查证明,确实有许多神经病、精神病患者在得病之后仍然取得了可观的艺术创作成绩。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今尚无公认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天才的创造与精神病不存在必然联系。另一方面,确实存在着精神病影响下进行创造活动的艺术家。在欧洲,曾经出现过多位病后获得成功的艺术家,例如保加利亚的一位画家,在得病之后改变了他的绘画色调,“更加频繁地运用明亮的色彩,构图较少程式化了”。 杭州和南京的医院检查确诊,沙耆患有精神分裂症。据他的家属介绍,沙耆病情的特点是“逻辑思维混乱而感情完全正常”。他一般是上午清醒,下午糊涂,但不论清醒还是糊涂,他都在画画。沙耆在患病时也经常“写生”,但出现在画面上的形往往与写生的对象关系不大。从具体作品看,有一些显然是在逻辑思维完全混乱的情况下画的,而另外一些画则显得相当理智和清醒。从他患病以后的整体创作状态看,精神失常并未使他画出那种神秘、诡异、奇幻的,心理学家所谓的“精神分裂症艺术”。从他留欧时期的作品与他晚期作品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早年养成的有关绘画的一些基本规则和技法特色,如构图、色彩、笔触、人体结构等等,不但存在于他清醒时完成的画里,也部分地存在于他狂乱是完成的画里。但他的作品中最受画家和批评家赞赏的那一部分,显然是在相对清醒的精神状态下完成的。在那些画上,我们确实看到了更加明亮的色彩与突破程式化的结构。
三、从传统文化角度看沙耆 沙耆的成就决不仅仅倚仗他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所独有的宁静和自由。在国内学画时,他的绘画才能机已经被发现。他在欧洲艺术环境中连续停留了近十年,在众多留学归国的油画家中间,只有他和李铁夫有过这样持久、深入地研究西方绘画艺术的经历。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去国外求学只是他的艺术事业的准备阶段,他的主要“战绩”应该从他的学业结束时开始。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中国油画家最具水准的作品却是他们在国外美术学校里的课堂作业。他们在离开课堂之后的作品,往往大失水准。如果不是明白无误的作品年代记在,几乎会使人误以为那是进入美术院校接受专业训练之前的作品。除了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之外,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艺术环境,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绘画不是单纯的手艺,它更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不同文明体系中生成的造型艺术,依附于不停文明体系二存在和发展。留学数年回国的青年画家带回来的是某种脱离了母土的苗木,这些苗木的生机取决于青年画家的艺术才能和从事艺术的毅力、韧性。沙耆不缺少才能,也不缺少这种毅力和韧性,虽然那是由于健康原因而被扭曲了的毅力和韧性。 就留学时期的学业成绩说,沙耆属于成绩优异的留学生之列。在李铁夫、徐悲鸿、吕斯百、吴作人……这一场串,名字之中,应该加上沙耆的名字。就留学归来“第二次创业”的成绩说,沙耆更是闪烁着独特光彩的画家,他可以与吴大羽、吴作人、董希文、吴冠中等人并列而无愧。 他在患病以后创作的许多绘画,其艺术力量绝对不在“身心健康”的同行的绘画之下。就他本人的感情世界来说,他的特殊处境似乎使他免除了常人无法摆脱的心理上的焦炉和极度抑制,而接近庄子所说的“坐忘”、“忘知”境界,即淡忘世俗的礼、法、利、害而接近精神的自由。用雅克.马利坦的话说,是“诗性直觉”和“诗性经验”引导着他画出那些足以引起人们艺术共鸣的绘画作品。
四、沙耆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位置 沙耆的精神疾患使他远离政治运动,同时也就远离政治迫害;使他远离充溢于美术界的思想偏狭;使他远离“三突出”“三结合”“红光亮”之类的戒咒,其实就是远离了一种集体的癫狂。 沙耆没有自觉地参与现代某流派的艺术探索,也与30至40年代国内那些前卫艺术体没有任何联系,我们没有听到他对欧洲现代艺术以及国内30年代上海的“决澜社”、广州的“中华独立艺术学会”和40年代重庆的“独立画展”有何看法。在组织和言论上,他不是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弄潮儿。但从艺术实践的角度看,20世纪前期倡导现代艺术的干将,如倪贻德、庞薰琴、梁锡鸿、赵兽等人,都由于环境的限制而未能将他们处于萌芽状态的艺术充分展开,未能将他们的艺术主张贯彻始终。相形之下,经由个人情性自然进入现代艺术天地的沙耆,在艺术实践上要持久和深入得多,在艺术成果上也丰富得多。 始终保持了独立地艺术立场的林风眠、吴大羽,也与沙耆的艺术历程不同。林、吴二人是清醒的探索者,他们的作品时他们的邪说和理想完成的。而沙耆的艺术史生命遭受挫折时的自然流溢,他的绘画是“不能不为”,“有所不能自己”的产物,因而具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独特情貌。这显然是可慕而不可学的。许多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都曾论及中国现代艺术“原创性”的匮乏,确实,我们的各种现代、后现代风格,往往都出于对西方艺术的追随和模仿。但沙耆的艺术不在此列,沙耆是以自己的生命遭遇浇灌艺术之树的人。 在20 世界中国艺坛,人们过多地关切艺术的社会效益。这固然是针对近几百年来文人艺术之游离于现实社会的一种矫枉过正,但它付出的代价是消弱甚至丧失了艺术最可贵的独立和自由的品格。50年代以后,主流美术界倚仗政治权威要求于美术家的,实际上并不是个人思想感情的真挚,而是个人选择了哪一个“人格面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沙耆出现在艺术史上。由于他的出现,我们不能不正视20世纪中国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可以说,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沙耆替他的同辈和同行发出了“感天动地”的伤痛呼号。 如果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曾经有过伟大的艺术家的话,沙耆应是当之无愧的伟大艺术家。 今年是沙耆先生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沙耆先生。杜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