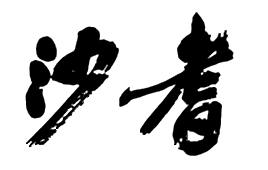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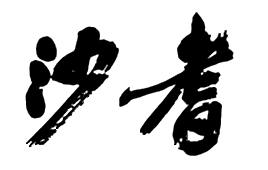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范景中
美术之友
2002.1
这是一次特殊的画展,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个特殊的人,他那特殊的生活经历和他那特殊的绘画主题,曾经给予研究过他的人一种特殊的魅力。但是,我们现在把他的作品展示给大家,则是希望观众能够领略:杰出的作品是如何超越了特殊的个人而具有丰富人们心灵的普遍意义。

作为一位艺术家沙耆早年曾是刘海粟和徐悲鸿的学生,也曾在林风眠主持的国立艺术院有过短暂的学习。1937年,他负笈比利时学画,一去就是十年。正是在那里,他的作品曾和毕加索等人联袂展出。他把东方的豁达襟怀和悲悯的同情心灌注到委拉斯开兹和戈雅式的技巧当中。这种做法不仅使他较早地加入了探索中国美术出路的先行者行列。而且也为他在布鲁塞尔的1e PetiteGalerie的几次画展中赢得了荣耀,为中西融合的美术之路写下了难得的一章。
遗憾的是,这些闪光的篇章已长期被人遗忘。他那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子像》,他那构图别致的《艺术家全家像》,就像缥缈的轻烟消逝在历史的幕后,艺术家本人也长期孤寂地生活在精神病院和乡村农屋。这时期他的一些绘画主题表明,他经常要对付的最可怕的敌人就是始终盘旋在内心的忧郁情绪,这种情绪常常使他想到古老的时代。例如,想到神话中的特修斯和阿里阿德涅,那时高傲的英雄赢得了爱慕,自然使他着迷、使他倾心。不过,他也经常希望具有一种勇猛精进的气概,因此也不断地把自己象征成一只老虎,幻想着在一种创作的狂热之中。他不仅画他喜爱的人体,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平凡常见的图像。然而,即使是那些普通的风景和静物也总是散发出一种浓郁而强烈的气息。但是,在他的绘画中更为强烈动人的是作品所猛烈燃烧着的激情。无疑,它有时流露出了艺术家因受到压抑而更加炽烈的不幸爱情。也许,正是为了这种爱情,他的绘画也越来越变成了一种色彩的象征。甚至使我们觉得,他要用色彩的威力,来表达他内心难以遏制的冲动,并且为了这种冲动,常常不惜抛弃他往日苦心孤诣所学来的素描技巧和构图规则。我们知道,正是这些技艺,为他早年在欧洲赢来了声誉,成了他与伟大的艺术家相埒的凭证。而现在他要让色彩的光芒照亮他所幻化的世界,也许只有在那里,他才会欣然地凝视他所赞美的景象:
我全神贯注地看着比亚特丽斯,但她光彩璀璨以至使我感到神迷目眩。-神曲·天堂篇,Ⅲ,127-9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此而把这些作品看成是艺术家自我表现的心血来潮。且不说爱的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普遍价值,且不说任何自我表现都不能解释人的天资。单就绘画本身而言,浮现在艺术家脑海中的就绝不仅仅是自己的情感经历。显然,还有形成作品的传统和所面临的艺术问题。因此,在理解一个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的绘画何以不同于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涂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凡·高的告诫:不要以为我故意拼命工作,使自己进入一种发狂的状态。相反,请记住,我被一个微妙的色彩平衡所吸引。这一告诫正是艺术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声音,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文明就会黯然失色。
不难体会,就是这些绘画本身的问题,不仅成了沙耆心灵的慰藉,也成了他在孤独中显现庄严的方式,成了他超越自我的方式。尽管艺术家的手也像但丁笔下的艺匠那样会不时颤抖,但他却在90年代还为我们创作出了一幅幅气势恢宏的杰作。
我们将看到,这些作品是一些辉煌的色彩交响,而它的配器则是印象主义、野兽主义、表现主义、甚至抽象主义。总之,不论他采用什么手段,都似乎在用色彩来激动人心。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他往往缺乏称心如意的工具,往往缺乏想急于使用的颜料。然而他那粗陋的指挥棒却像沾濡了神的恩典,简单的几笔也会骤然化作眩人眼目的形象。因此在画出色彩的震撼力上,几乎没有几个中国的油画家能和他相比。不过他却从来没有摆出创新者的姿态,更无意引起新闻界的注意。事实上,他几乎已不再指望人们看他的画了,就像塞尚和凡·高一样,他要画下去,只是因为他不能不画。
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就此停笔。这篇短序意在勾勒出一幅沙耆的印象式速写,要想深入理解他的精神世界,最好是去看他的作品-那是由一系列的杰作构成的艺术家的思想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