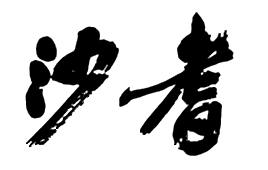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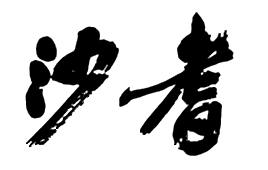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范景中
美术
2001.4
艺术是一种不可言喻的东西,它们的创作者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他们有非凡的才华,却受到压抑;他们有神性的创世才能,却受到贫穷与孤独的磨砺;他们生不逢时,死后却荣誉纷至沓来,辉耀青史。这种观念经过浪漫主义的渲染,已经成了撰写艺术家传记的常用模式。我们在这里介绍的沙耆,也带有几分这样的色彩。
沙耆是中国最早留学比利时的油画家之一。他旅欧十年,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在油画艺术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的作品曾多次与毕加索等大师共同展出,并在比利时各重要的美术馆举办个展,得到舆论界的高度赞扬,一度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艺术家。
沙耆1946年回国后,徐悲鸿即聘请他为北平艺专教授,但由于疾病缠身,未能上任。嗣后,他长期蛰居自己的故乡--浙江鄞县沙村,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严重的精神疾病,虽然给他的日常生活蒙上深深的阴影,但并没有浇冷他对艺术的炽热之情。在一座破落的村舍里,他拿起画笔,在旧书废纸、残壁败墙、床板门板、家具什物上不停地画着写着,没有空隙就在书上作画--他就这样默默地工作了30多个春秋。
然而,苍天有情,这位饱受心灵创伤,几乎被人遗忘的画家,竟然在他的晚年,奇迹般地出现在中国画坛上。1983年,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省分会先后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举办了"沙耆画展",展出了沙耆早年旅欧的40多幅油画,整个画坛为之震动。他那坚实的造型、沉郁的色彩,唤起了年迈古稀的老画家对传统的美好追忆,也让那些处于极度的创新亢奋状态之中的年轻一代艺术家瞠目结舌,大家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功底深厚的画家而感到惊奇。的确,在20世纪画坛上,像沙耆这样能如此纯熟地运用古典主义手法的画家,真是寥若晨星。
展览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沙耆的生活境遇,但没有改变他对艺术的忘我之情。他依然离群索居,默默无闻地工作。80年代中期,沙耆画了一大批用笔率真、色彩纯朴的写生作品,还不时用彩墨作些花卉畜兽,甚至挥毫作书(沙耆书法豪迈俊逸,与其堂兄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一样,多得益于苏轼),以泻胸中的积郁之情。
到了90年代,他的画风幡然一变,他集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之大成,自出机杼,创造出了一幅幅气势恢宏的伟大作品。他的画面是那样绚丽、那样光彩夺目。尽管他往往缺乏自己想用的那些颜料,但是在画出色彩的震撼力上,没有几个中国的油画家能和他相比。他唤起色彩本身的威力,来表达自己内心难以遏制的冲动。甚至,为了这种冲动,他不惜抛弃了他往昔苦心孤诣学来的素描技巧和造型规则。我们知道,正是那些技巧,为他早年在欧洲赢来了无上的荣誉,成为了他跻身于伟大艺术家行列的凭证。然而,沙耆晚年的这些作品的魅力不仅仅在他那耀眼的色彩,因为在他那沉着痛快的笔触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中国画内在的精神--神韵。正是为了捕捉这种神韵,无数的中国画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也正是为了向西方观众解释这种神韵,我们的学者感到了语言的苍白和抗译性。
笔走于此,我想到了中西艺术的融合问题。恕我直言,对20世纪以来中国画坛的这种探索的成果,不敢恭维。到底说,这种融合,大都停留在简单的"翻译"上,不过是用油画的材料去表现水墨画的形式,或者用水墨画的材料来表现油画的风格。这种"硬译"的结果,使我们失去了艺术中最珍贵的东西:"趣味纯正"。也许,黄宾虹是个例外。他晚年作山水时,参酌了印象派的某些视觉原理,使画面显得更加浑厚华滋、扑朔迷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用谢赫的"六法"、黄休复的"四格"、董其昌的"二宗"去品鉴和诠释它们。如果说,在"中西融合"方面,黄宾虹是水墨画界的一个成功的例外的话,那么,沙耆便是油画界的一个成功的例外。我们完全可以沿着莫奈、凡·高、马蒂斯的目光,来欣赏沙耆晚年这些精彩绝伦的油画。在黄宾虹和沙耆这种例外的成功背后,还有这样一个相似的例外--"衰年变法"。我相信,只有像黄宾虹和沙耆这样在某一传统方面积学深厚的画家,才能在另一传统中真正发现有益这一传统扩展的空间。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沙耆是中国现代油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沙耆的杰出不止于他艺术方面的才华。他从来没有要向世人炫耀自己的这种才华,更不想引起新闻界的注意。事实上,他几乎已不再指望人们看他的画了,就像塞尚和凡·高一样,他要画下去只是因为他不能不画。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就此停笔。这篇文章意在勾出一幅沙耆的印象式速写,要深入地了解他的精神世界,最好是去看他的作品--那是由一系列杰作构成的艺术家的思想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