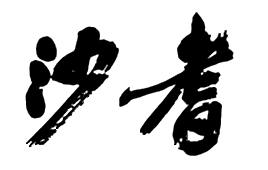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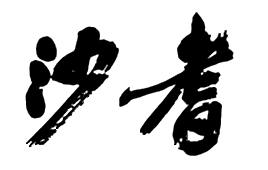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范景中
中国时报
2001年
但是,恩索尔和皮尔梅克(Constant Permeke)、塞伏兰克斯(Victor Sevranckx)是当时比利时学院派之外的最著名人物,他们正叱咤风云,驰骋画坛。如果说他们的表现主义,他们的幻想手段,他们的抽象色彩,一点也没给沙耆留下任何印象,在今天看来,也是不真实的。而且不仅如此,我们认为,连同上述的一切反学院派,反古典主义的运动(尽管这些运动主要发生在巴黎),都肯定给沙耆留下了印象,并且这种印象的潜力如此之强,以至在他日后的艰难岁月中终于聚变成了能量。这一切就是决定着沙耆的选择范围和选择方向的艺术情境。
但是选择本身不可能完全由外界决定,选择是艺术家自己做出的。他为什么最终放弃了古典主义,用色彩压抑了素描?要追溯这些植根于个人往日的经历和个性的原因,要刺探这些隐情,也许只有心理学家才能胜任。因此,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一段话也许让我们有了一个解答问题的希望。他说:
正如分封中的蜂群,它们一直层层叠叠地挨在一起,靠在前面不多的几个蜜蜂上,这几个蜜蜂的脚紧紧抓住蜂群悬挂在上面存身的树枝;我们思考的对象也是这样--它们通过一个个联想环节相互附联在一起,但是它们全体的原始来源是最早的一个对象曾萦怀的兴趣。
在沙耆后半个艺术生涯中,他所萦萦于怀的是什么呢?正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他的家庭悲剧。这场悲剧是在他去国十年、狂喜而归时发生的,当他面对人去楼空、四下茫茫的一切时,他的悲剧达到了极点。他想长歌当哭,他想迎风长啸,他想粉碎眼前的阴霾,他想驱散他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就是他的绘画所给予我们的印象。这样,他的画中便出现了一些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心理分析的题材,例如那些既象征着爱情又象征着邪恶的苹果,和那些也许折射着白日梦的人体(这一点也许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临摹的《泉》中所删除的东西和所添加的东西),甚至他先后选择的古典主义的硬性和浪漫主义的软性也能结出丰富的分析性果实。他在粉壁上挥写的古代贤哲的浪漫巨篇《离骚》,既营造了一种幻境纵横之上,又映证了他默默无闻的孤绝生活。也许正是在无边的寂寞中所澎湃的难以遏制的激情使他毅然抛弃了早期画风,而代之以一种对立的风格。这样,不仅他所选择的题材,而且连同他所选择的风格都成了意义的载体,成了情感交流的符号,通过这种媒介,艺术家把他的精神客观化,而我们也据此理解了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因此,历史女神不只造就[忧郁的天才](melancholaingenii),而且也提供给他表现的程式,没有这些程式,我们就会对艺术和艺术家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