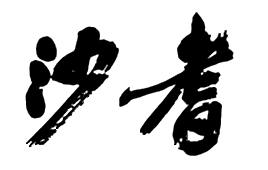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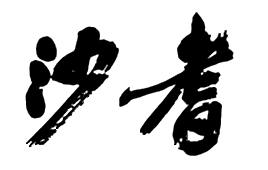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范景中
中国时报
2001年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一时期的几幅作品,就不难发现,色彩的表现力确实已成了沙耆思考的主要内容。在这些画上,红色、黑色和蓝色得到了一再的发挥,而且使用得如此激动人心,甚至使人想起了波德莱尔(Baudelaire),用词语所做出来的那种色彩组合,例如:『黑色的夜晚,红色的黎明』;『黑色的空无,血色的残阳』等等。
我们有时不免怀疑,沙耆可能读过这些诗句。也许,是梵谷(Van Gogh)所谓的"要用蓝色和红色表现人类的恐惧心理",或"色彩能暗示某种具有热情气质的激动"之类的宣称,涌上他的心头,使他对色彩进行了如此深入的思考。
勿庸置疑,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论立足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具有一种感情,它随后能以一种符号或色彩的形式被表现或挤压出来;方向是从内向外,彷佛是离心的放射。然而古典主义的理论则强调了另一方面。在《哈姆雷特》中有一场戏中戏,在那场戏中,埃涅阿斯(Aeneas)告诉迦太基王后,特洛伊的国王是如何在他妻子赫卡柏(Hecuba)面前被杀的。在讲述这个令人恐怖的故事时,演员自己面色苍白,泪水盈眶。于是,哈姆雷特思考了想象力的作用,并问道:"赫卡柏是他的什么人,他竟为她而哭泣?"显然,演员不是因为他为特洛伊王后感到悲伤而哭泣的。他是通过背诵剧本的台词进入感情的。这是一个向心而非离心的过程,换言之,不是悲伤引起了充满感情的台词,恰恰相反,而是充满感情的台词引起了悲伤。正如伟大的英国批评家理查兹(I.A. Richards)在他自己转向诗歌写作后日益所强调的那样:是语言赋予诗人以灵感。诗人的媒介是他的语言;他只能表现语言为他提供了表现它们的词语或形式的那些思想或情感。他的艺术在于通过选择最接近他想表现的事情的适当的词语、语调或形式来使他的媒介服从他的目的。但是认为他的感情居先那便是过于简单化了,情况往往是,语言在不断的相互作用的活动中启发和激起他的感情。如果我们说,波德莱尔或凡高的语句激发了沙耆用色彩表现他的感情;或者用绘画的语言说,是委托斯克斯的笔触,伦勃朗的暗影和戈雅诡谲左右了沙耆绘画的发展方向,那么我们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意见。实际上,浪漫主义因素早在沙耆留学比利时期间就已进入了他的心灵,而且在1942年3月举办的画展简介中都有所透露。简介中这样写道:
沙耆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下受益匪浅。一个是对国内生活的关心和豁达的人生观所形成的同情心的影响;另一个是与那些伟大人物,例如沙耆敬仰的委托斯克斯、伦勃朗、戈雅等人的接触的影响。
可以说,是传统,是艺术程式,或者说是媒介为艺术家提供了选择,使之借以表现他们心灵的趋向。就此而言,甚至连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简单对立公式,也包含了形形色色的象征符号,可以供艺术家去拣选,正像在英国查理一世和议会的战争期间(1642-1649),长发和圆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选择,能表示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倾向一样。
然而,即使是一座秩序井然的古典主义的神殿,一旦残破倾圮,它便具有了浪漫的意义。因为,从断垣破壁中领略出美的眼光,正是浪漫主义的眼光。与此类似,我们从沙耆临摹的安格尔的两幅画《泉》和《安德洛玛达》(Andromeda)上看到的也正是艺术家所投射进的浪漫主义眼光。换言之,在沙耆的笔下,两幅古典主义的名作均被转换成了典型的浪漫主义或者表现主义的作品,令人想到了雷东(Odlon Redon,1840-1916)和凡东根(Van Dongen,1877-1968)等人笔下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幅画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它们为我们指明了理解他晚期作品的线索,正如他早期临摹的《马拉之死》提供了理解他早期作品的线索一样。
艺术家为什么要在这两种风格中做替换选择?难道艺术家果真对这两种风格的对立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影响了他的表现意向?要阐述这些问题就需要另写一篇文章。不过,我们无需沙耆本人作证,也能猜测出一些历史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艺术家留学期间巴黎美术界的情境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战尽管时过境迁,但在美术界,特别是在美术学院所激起的波澜则还未平息;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尽管力图能摆脱那场争论的牢笼,但他们摆脱不了它的阴影也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的学院派古典主义势力仍很强大,甚至比我们想像的还强大。如果说这种力量已被我们忽视,那正是现代艺术运动发现的结果,正是这种运动把诸如达仰、巴斯天(A.Bastien),甚至布格罗(A.W.Bouguereau)那样的学院派领袖推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我们追溯这段历史则不能让他们依然居于艺术的边缘。另一方面,从19世纪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前,法国始终是欧洲美术的中心,是艺术朝拜者的圣地。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比利时美术就是法国美术的翻版,这就是一些年轻的比利时画家例如考克(Jan Cox)、德尔沃(Paul Delvaux)和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经常奔波往返于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重述一下沙耆离国赴欧时所怀有的抱负。可以说,他的老师徐悲鸿的警句"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我们不难证明这里所谓的写实主义即欧洲学院派的古典主义),就是他此行的最主要的指导思想。我们前面引述的信件已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因此,他也像他的老师一样抱有下述的观念是不足为奇的。
研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艺术,以素描为基础;科学无国界,而艺术尤为天下的公共语言。
这样,尽管当时恩索尔(James Ensor)以他那揭露人性丑陋与虚伪的假面形象震惊比利时乃至欧洲的画坛,沙耆却象无动于衷一样,仍然精心地临摹布鲁塞尔所拥有的古典主义实物《马拉之死》,并精心地绘制诸如像我们前面所述及地《年轻女子像》,那样端壮美丽的作品,其意义就远不止单纯的画面所给予我们的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