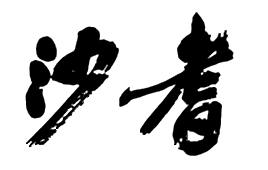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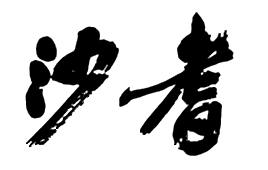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范景中
中国时报
2001年
编案沙耆
沙耆,一九一四年生,浙江鄞县人,是当代中国画坛的悲剧性人物,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早年家境优渥,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少壮赴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深造,在中西画艺上都得到良好而完善的训练。
沙耆在一九三七年告别新婚妻子出国,两年后毕业,在欧陆举行多次个展,沉浸于西方艺术的探索,作品甚受肯定,殊不料他专注于画艺精进期间,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已毁灭了他的故乡。一九四六年,他学成返国,只发现十年来音讯断绝,自己已落得家破人亡,爱妻与儿子不知去向,父亲也病故,他在打击下精神失常,遂以绘画为唯一的生命寄托。曾有一次,上海留比利时同学会聚会,沙耆前去参加,一句话也没说,只顾画画,同学会结束大家各自返家,沙耆却还在公园里画个不停。
他在疯狂错乱与拮据财力中,执着地以油漆、胶泥在邻舍的门板、垣墙上作画,不幸许多作品在文革期间横遭破坏,大量散失。一九八三年得朋友协助,重新举办个展,他以充满激情的艺术语言诉说对生命与爱情渴望的华美创作,才再度赢得广泛的注意。目前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二楼的[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展出沙耆的作品七十九件,乃沙耆的画首度在台湾展览,是亲历其境体会深邃的绘画魅力不可多得的机会,画展至四月廿九日结束。
沙耆的早期绘画虽然不时地闪现出色彩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基本被压抑了,因此他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古典主义压抑了浪漫主义。沙耆的晚期绘画特别是九十年代前后的绘画,和他早期的古典主义倾向相比,虽然主题仍旧是传统的,但是色彩却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完全压抑了素描和构图,并获得了一种令人惊叹的效果:在整体画面的明亮之中保持了个别色彩的独立价值。
在中国,书信是长辈教育子女的一种常用工具,长辈的亲子之爱,寄托之情,往往于兹可见。在沙耆先生保存的信件中,我们也看到了一封这样的信。那是他的父亲藜斋先生的教子书,信的主要内容由抄录宋代张来(1054-1114)的<送秦少章赴临安簿序>构成。藜斋先生说:"录此寄汝,其熟读之,自知余之所以慰汝者。而望汝者,则在此也。"从张来的序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话:
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迁之为贵,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则归不能霸;子胥不奔,则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羁穷忧患之时,阴益其所短而进其所不能者,非如学于口耳者之浅浅也。
藜斋先生引用的这些话,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像是应验了的预言。沙耆先生正是由于负笈欧洲十年,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或许在沙耆的艺术世界中看到的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因此,可以说历史女神不仅用孤寂使其行拂乱其所为,而且也用孤寂使其艺术放射出了庄严的光辉。沙耆先生在比利时的学习生活,我们所知不多,但从他那时所画的作品来看,大致和他在赴欧之前所接受的徐悲鸿带来的法国学院派画风一脉相承。他那时期的油画虽然在用笔和用色上显示出了印象派的影响,甚至令人想起鲁本斯(Rubens)的奔放笔触,但总体上还是重视素描的主导作用,因而在造型上采用的是较为严谨的写实手法,用色则强调冷暖色彩的立体法所产生的三度空间,构图平稳而均衡,并不时呈现出一种静穆和单纯的格调。简而言之,沙耆力求达到的是古典的和谐,正如Stephane Rey在评论他于1945年5月在Bruxelles Louis大街Le Petite Galerie举办的画展时所指出的那样:
这位绘画高手采用的手法构图确切,色彩文雅,不拘一格,而且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和谐……其风格朴实、匀称,给人以罕见的真实感。
他的《年轻女子像》(法文为Portrait de jeune fille)画的是一位姿态优雅的正面少女,婉容绰约,双目炯炯,头部微微斜侧,很是动人。构图为典型的金字塔式,这正是古典肖像的常用程序。不过整幅画的灵感也许来自威尼斯大师提香(Titian)的《花神》。
《艺术家全家像》(法文名Portrait d une famville d artistes)则显示了印象派的影响。他把其中一个人物安排在左部的边缘,大概是想从一个意外的角度去画出空间感,这令人想起了德加(Edgar Degas)的室内人物群像。德加对构图法和素描法有强烈的兴趣,并真诚地赞美安格尔(Ingres)。这种态度显然也是沙耆所赞赏的态度。因为,尽管他十分喜爱印象派所发展起来的色彩,但是以素描为造型基础的信念他却没有动摇。这种信念也许并不合乎他的天性,但是从徐悲鸿和吴作人先生给他的信中(这些信件是一些珍贵的文献,我们将在后面述及),我们知道,这正是他的老师和他的师兄对他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古典主义的哲学强调cogitoergo sum(我思故我在),强调概念、理式或Idea的主导地位,强调分析和推理的力量,而把现象和体验推到了真实世界的边缘。这反映在绘画上即是强调素描(dessin),认为素描才是真正的画图(tableau),认为只有线条才能再现物体的范围(L'etendu),使绘画得以成立,而色彩不过是表面的装饰(ornement)而已。
这种古典主义的重素描、轻色彩的艺术观早在瓦萨里的《名人传》里就得到了强调,在那部著名的书中,他用这种观点评论了佛罗伦萨画派和威尼斯画派。这种态度影响了17世纪的普森派(Poussinistes)和鲁本斯派的争论,并传递到19世纪的安格尔派和德拉克洛瓦派的对立,甚至沃尔夫林(H.Wolfflin)的线描性和彩绘性的概念似乎也渊源于此。
了解了这种传统,我们便可以对沙耆的早期绘画下一个简单的结论:他的绘画虽然不时地闪现出色彩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基本被压抑了;因此他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古典主义压抑了浪漫主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转向沙耆先生留学初期他的中国老师徐悲鸿老师给他的一封长信:
弟于美学尚未见其全,今略有以示弟。美乃一抽象名词,并无那样东西,所谓美者在造物nature,为难得条件之备具。在艺术品为一种德性之完成。故艺术之美全非造物之美,惟造物之美使艺术家情绪活跃,因而兴起inspiration,如花之美必因其Fraicheur或因其形Forme错综,或因其各色分配之自然调和,如山、木树、清溪或落日,或以其高峻奇险,或因以其超拔苍郁,或因受光之明媚,或因其长空无垠而光采焕发,其中皆具一条件。至于艺术品,希腊古人则以其noblesse,鲁本斯则以其壮丽与雄强,米莱则以其真率Sinc erit e若落难,达文西则以其高妙,拉飞罗则以其静穆,米开朗基罗则以其高超与强固。原无论其为造物与艺术,而为美之惟一精髓乃是和谐Harmonie。
在指示了美即和谐这种古典主义观念之后,徐悲鸿先生特别提醒道:
弟应注意之点:古人大画家均为建筑家,今之画家亦必须学习建筑术。画中应用直线,于是Coloration可截然支配,不枝节显得琐碎;则自然伟观。有时且缀碎锦,以为m elodie 可研究V e nitiens,如帝襄、范乐耐是等作品。速写者非徒言写之速也。可多作小说插图,采取各种不同之形式,试为表情尽量之构图练习,必须十二分eloguent简单明了,为他日大成之基。
这里所强调的正是我们在上面所述的重素描、轻色彩的绘画观。从吴作人给沙耆的信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话:"兄寄近作中有颇佳者,惟亦有不够坚实者。作画不可迅速,不可随画随涂去。"(一月卅一日信)也许是沙耆不时地流露出逸笔草草的浪漫倾向的缘故,吴作人连寄几函加以劝诫,读来令人感动:
闻兄在比极奋勤学,深为欣慰。BASTIAN师曾来函说起兄努力,并引以为快。说"兄工作极速,甚至于是太快"。不过"太快"是缺点。看寄来之近作之照相,Copie甚佳,Portrait用笔流畅,调子也准确,但是头与肩的比例不甚全称,恐怕是画太快所致。尤是应注意在五官的部位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画像贵能传神,切不可了草。Dessin为基础的一切,不可须臾离也。画人(有衣的无论在什么动念)必须假定他是Nu,是否站得住。画Nu须要假定去了肌肉,他的骨架正不正确,这种检讨,我们就叫做Dessin。在法文中说一张画Manque de dessin就是说"没有骨子",缺乏内容(讲技巧时),就不免泛然了。广观历代大家,尤其是Primitif Flamands,他们对于Dessin,刻实的精神,令人服倒。因有殷望于吾兄,弟故不惮叨叨。幸兄勉之!(11月26日信)。
看了这些信件,我们不难体会沙耆是怎样磨灭浪漫的锋芒,而精勤不懈地务实素描的根基了。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再来看沙耆的晚期绘画,特别是90年代前后的绘画,就会别有发现。和他早期的古典主义倾向相比,虽然主题仍旧是传统的,但是色彩却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完全压抑了素描和构图,并获得了一种令人惊叹的效果:在整体画面的明亮之中保持了个别色彩的独立价值。
这种倾向在他大概画于80年代的一幅人体上已见端倪。在那幅画上,与其说是造型,不如说是色彩的响亮引起了人们共鸣的强度。可以说,那是一幅典型的鲁本斯风格的作品。它不再是精心地使用色彩塑造素描,而是用"彩绘性的"(Painterly)手段快速绘就,这种手段十分有力地加强了生命和活力的感觉,尽管我们没有看到被画人物的脸面。
从此以后,他的色彩似乎日益简化,日益饱和,并往往用浓重的颜料画出一种抽象的造型韵律。用本世纪原始主义的比喻性术语来说,即是像阿拉伯式的纹样(Arabesque),或者像拜占廷马赛克(Mosaic)的鲜明色块的镶嵌。我们看到,他在1994年和1995年之间所绘的几幅水果静物已然抛弃了传统的复杂构图,也不在光影塑造上狠下功夫,而是发挥笔触的力量,如水泻泉涌,造成一种凌乱飙飞的辉煌色彩,并给人一种直接观察得来的效果。
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在评论塞尚时指出,黑色是塞尚超越印象主义的征兆,因为他打破了印象主义的棱光七色,不仅描绘光线,而且也同时描绘"住在空间的"物体。这种说法也完全可以移用来评价沙耆在1994年11月所绘的一幅花卉静物。我们看到,画家通过色彩的单纯化,给所绘对象一种强烈的形式感,笔触连贯的黑色不仅强化了物体所在空间,而且根本无视与现实的关联。更令人震惊的是,它与背景的绿色形成的强烈对照,大片的色域几乎完全以平涂的手法画出,显示了画家在有意识地强调纯色的心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