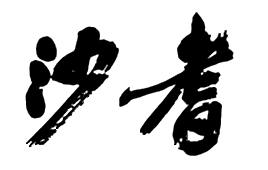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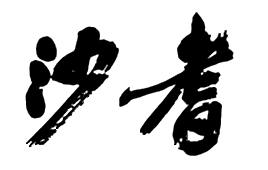

朱青生
新美术
1999(1)
根据《沙耆传》(载《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员传略》第三辑,227 - 233页),沙耆画展《前言》(1983),陈鹏举、沙洲《访沙耆》(《解放时报》1983年7月12日),吴作人题跋(1983年8月),沙洲、朱良仪《画家和农民》(《文汇报》1983年7月20日),徐秉令《沙耆先生今何在》(《现代中国》1994年5月,56-57页),艾中信《沙耆画册·序》(手稿,未注日期)得知:
1.沙耆学习油画,在比利时留学,并在留学期间取得成就。
2.沙耆1946年回国,因为家庭和健康等原因未任学院教授,回到旧籍浙江鄞县沙村。
3.沙耆1952年以后受到政府的关照,并于1953年徐悲鸿去世后被遗忘,但他在乡间极艰难的情况下每日画画。
4.沙耆1983年重新被重视。
这些事实说明许多问题,也暗示着许多有待调查的问题:
针对1.沙耆从巴斯蒂安〔A. Bastien )处学到的艺术是什么?两年之后毕业得奖是因为画得像欧洲人还是因为他画里带进去了本土文化的因素?他在滑铁卢区的10平方米画室工作了7年,画廊、收藏者和评论家一直怎样对待他的艺术?以及他自己对当时艺术的评判和选择,对战后艺术变更的参与程度又如何?
针对2.沙耆的健康原因在诸多事件中的作用。他患的精神性疾病,得病原因可追溯到1932年因请愿、宣传抗日被捕入狱得保释之时,此后病情加重。此为影响其家庭、就职和作为艺术家社会正常活动的主要原因。按他自己的说法,则得病在先(《沙耆传》232页)。这在旅欧期间不知是否对他有所影响?
针对3.沙耆1952年因为周恩来总理的过问和徐悲鸿的关心得到政府津贴,一直执行到"文革"开始(《沙耆传》),之后才穷得连木炭笔都买不起,就砸了家具烧成炭在墙上作画。但是他并未为人所"遗忘",尚有族兄沙孟海关照。应该认为他只是因病不能从事正常的社会工作。
针对4.一旦有机会,在沙孟海的主持和影响下,在同代师友同仁的协助下,迅速出名。在上述诸多问题调查清楚之前,对沙耆作品的分析只能是初步的。但是,即使是初步的研究,也能反映一个有文化背景的人在接受另一种文化方式时的规则--主动误取。在沙耆的艺术中,有一部分是采用油画并在室外写生(前引诸文皆强调了这一点),现在从沙耆风景写生中可以理出一个论题:
在中国学的西方的油画→巴斯蒂安影响下的油画(间接的佛莱芒画派影响;印象画派影响) →外光与在自然光线下的色彩冷暖关系的着重(自觉理解了的或被传习到的) →回中国后的油画保留着色彩冷暖关系(例证I):遗失色彩冷暖关系而只有固有色的明暗关系(例证II)。
例证I:《雪景》,1986,油画,?X?,上有"丙寅年八六年沙耆"款。
分析:以暖调子为主。天色偏暖,中间楼房山墙冷灰色,而楼房的另一面是暖褐色。近景雪的受光部偏暖,背阴部呈现为偏黄的和偏青的两种对峙状况。色调控制是有节度的,在他的调色板上有纯度很强的色彩(用于题款的红色),但都在合适的冷暖对比中,调和后排入画面。总之,典型的印象派以后的欧洲色彩画派。此画从调子、题材和雪的笔触处理都可追溯到西斯莱的《雪景》。
例证II:《湖边风景》,?年,油画,?X?,无款。
分析:以蓝绿色为主。天色和水的处理没有冷暖,直接按固有色画出。中间近水的两棵树的树杆用树皮的固有色(棕色),水边的人也用固有色(红色)。在视觉上是不能观测到这么强的纯色(对象衣服固有色也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为了"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固定色彩程式。总之,典型的年画配色法。虽然材料是油画,笔法是莫奈中期风格,题材也是印象派惯用的天光水色,但是完全遗失了色彩中的冷暖关系。
例证I和例证II中的对比分析:
沙耆回国后,同时使用两种色彩方法:冷暖色法和固有色法。冷暖色法的笔法色彩皆从西方引入,而固有色法的笔法从西方引入,色彩却变更了。至此,分析似乎已完成。
但是,注意到沙耆在中国所作的风景写生,除了《风雪》之外,几乎都是用固有色法。应该重视沙耆"中国画眼"的恢复的事实。也就是说沙耆在将冷暖法色彩引人中土之后,逐渐将之遗失,恢复了"随类赋彩"的年画传统,用固有色法作画。只有在少数特殊场景下,他才追忆起旅欧所习的冷暖色法,表明他的"印象一佛莱芒派画眼"曾被训练完成(西方美术史上印象派画眼也是在19世纪晚期才训练完成的),而且保存在他手眼之中。
为什么沙耆的冷暖色法会被遗忘?不能归之为受中国绘画或民间艺术的影响。因为他坚持用西法,即使在贫困之中也用炭条画(见前引证据)。也不能归之为受中国河山和文化的浸染。因为在他家里,归国早期(1949年前)他在墙上画油画人体(傅时强《沙耆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欢乐》,1984年6月17日《宁波日报》),归国晚期(1983年)他在"四周粉墙画满了人体,赤裸裸地而且大部分是欧洲妇女的人体。他在这里默默地度过了38个年头,每天第一个功课就是用他的炭笔勾画人体,从不间断。墙上已经找不到空隙可以作画了,他就用画笔精心修改着每一条曲线,追求着美。"(沙洲、朱良仪文)据此可知沙耆未遗忘油画,只是遗忘了冷暖色法:并未遗忘欧洲透视一解剖的造型和笔法,甚至形象,只是遗忘了色彩。
沙耆遗忘冷暖色法是因为他的眼前景色提供了明显的色彩对象。印象派的冷暖色法以两个对象为训练场所:1、巴黎灰白色的建筑基调和西部海洋性气候影响下明朗的天光。2、19世纪末北欧妇女白晰肤色,色彩亮丽的发色、瞳色和衣饰。在布鲁塞尔30-40年代,无论从传统还是从环境都可承接冷暖色法。而回到浙江鄞县沙村,潮湿温润的气候加强了黑白对立为主导的视觉因素,又使山色原野的灰调的明暗层次感强于色阶的变化。由于视觉同时是文化赋予的,水墨画的传统在这个环境之下不可能不起作用。沙耆的家传使之早年接受过水墨画(其父仔浦画山水,见《沙耆传》),于是对于作为油画家的沙耆来说,他必须抗拒这种带有文化习性和直观视觉环境的双重逼迫。从以上分析的两张作品上,得到的是沙耆的两个针对逼迫的对策。
例证I是一种对策,就是找取能够表达冷暖色法的视觉对象写生。《雪景》是一个机会,花卉也是专门设置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偶然的,所以这类风景画在沙耆的作品中所占比例很小,画面"洋气",与欧洲著名大师的名作有传承关系。
例证II是另一种对策,即主动误取。即用油画颜料调出的固有色和根据明暗关系变更的固有色群写生对象。这时的油画已不是美术史发展到印象派以后的冷暖色法的油画,而是用颜料按固有色法在户外写生。在写生中,形象是直观的,色彩是非直观的,甚至还带有年画和水墨画影响下的"中国画眼"的程式(万绿丛中一点红)。中国绘画中从未有过像西方油画颜料这样厚重丰富的种类和质量,中国绘画从未有过户外对景写生摄取的透视空间和物体质感表现。在保持颜色质量和写实程度的前提下,在冷暖色法无法执行时,用固有色法充任,形成沙耆的油画风景写生的特色。
这一个主动误取油画的过程清理之后,分析沙耆90年代的油画风景和静物就相当便利。这些作品是"固有色法"的发展。这些画与马蒂斯、德兰的野兽派色彩表面上都相似,实质上完全是两种色法的发展结果。德兰的《桥》,受光部为中黄(无论桥和水面),背光部为群青,典型的冷暖色法。马蒂斯《绿鼻子女像》(夫人像),脸部的红、绿、黄等强烈的色彩对比是根据冷暖色法强化出来的。而沙耆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以固有色的不同明度造型。(之所以用"绝大多数"这个词,是因为在对象出现显示冷暖色法偶然机会时,手眼中藏有此法的沙老也会突然流露出冷暖色法的形迹。)
分析至此,只是初步。因为已经遇到了更为深刻的一个问题,即沙耆在比利时的作品是否也带有固有色法,也藏有中国画眼?这些问题要在上述"针对I"都解决之后,才能开始分析。